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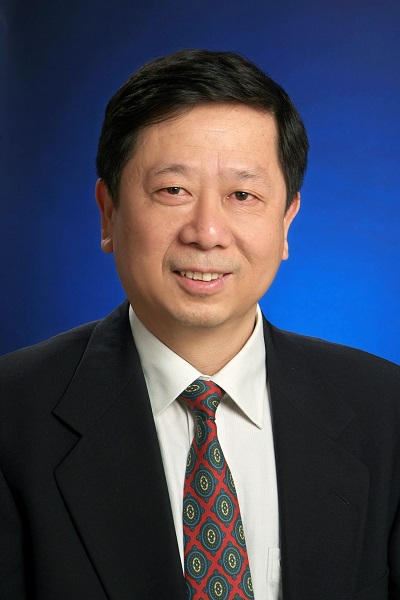
范模,1960年生,福建福州人。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舰船设计与制造专业,1982年毕业。先后在广州船厂、中海油研究总院工作。主持了3艘FPSO的设计,作为主要贡献者参与了8艘FPSO的自行设计;主持“浅水超大型浮式生产储油系统关键技术”国家863课题,解决了大型FPSO浅水应用的世界性难题;获得22项国家技术专利。2010年获船舶工业界最高荣誉“船舶设计大师”称号,是石油行业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在访谈中,范模谈到了1978年的高考盛况,埋头苦读的大学时代及大学生活点滴,也谈到了自己从南到北的工作轨迹及工作中钻牛角尖的趣事,对于成功与职业的选择,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诠释。
口述:范模
采访:欧七斤、漆姚敏
时间:2012年5月18日
地点: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(北京)
记录:漆姚敏
编者:漆姚敏
78级话高考
我的祖籍是福建省福州市,上中学之前,我在福州外婆家长大。我外婆家有5个舅舅,2个姨,除了最小的那个姨因为赶上“文革”没有上大学以外,其他都是大学毕业的。我父母五十年代大学毕业,分配在外地工作就回不去了。我是上到小学毕业后,大概1973年才从福州来到天津父母的身边。我跟交大的缘分?很简单,就是四年,这四年在上海交大上学。为什么会上交大?为什么会跟这个造船行业结下缘分呢?现在回想起来也比较简单,说实话是我舅舅的影响。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,我的几个舅舅选了军工行业的大学上,结果毕业以后全部分配到军工企业,去了三线,很偏远的地区,那个年代基本就很难回来了。后来舅舅就跟我说,你以后要上大学,不要选这种高端的专业,不然大学以后,可能就回不来。那个年代是统一分配的,不像现在是自己找单位。他说有两个专业可能不会跑到内地去,第一个是造船行业,第二个是纺织行业,其它的都不好说,包括钢铁厂都有往三线迁的。所以说,后来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定学校而是定专业。先选定这两个专业,然后去靠这个学校有没有这个专业,基本上是这样的。
回过来说高考,我是1978年高中应届毕业生,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。但是,1977年第一届高考我也参加了,当时在天津第八十二中学上学,报名的时候就是想试一把。高中内容没怎么学,就参加考试,具体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,反正是哪个学校都没录取。到了1978年高考的时候,我是下了好大力气去备考。当时是知道成绩后报志愿,挺好的。重点学校可以选10所,非重点学校也可以选10所,前后加起来20所学校,自由度很大。我父亲很崇拜高精尖的专业,考完后,我们一直在商量报考清华大学的核能物理专业。当时国家正在计划建设环形加速器,我也很想报清华的这个专业,在志愿表上把专业、学校名字都填好了,最后临交之前还是把它改掉了。我又想起我舅舅说的话,你要想留在沿海、留在大城市,你只能学这个专业,你选了高精尖专业后,今后可能就去偏远地区了。因为咱们国家只要跟军工有关的,只要跟高精尖有关的,按当时政策就是往三线调,往内地调,往偏远地方调。所以,我改志愿了。我上小学时我舅舅给我讲的这样几句话,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起了这样一个作用。以后,我就考去上海交大了。
应该来说,我们考上上海交大确实很不容易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报考状态了,后来有个统计,我们那一届报考跟录取的比例是后来再也没有过的,印象中是80几个人里面录取1个。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,因为是中断了10多年以后第一次高考,影响还没起来,报考人数还不是很多。真正有影响的时候是我们1978级,历年积压的好多人都来高考,考生中有工人、农民,干什么的都有,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比重反而不多。那时考取比例非常低,80多人取一个,要考上重点学校更不容易。
过得很快的大学4年
说起船舶专业,其实我对这个行业从小就比较喜欢。这可能跟小男孩的兴趣有点关系,小时候就喜欢一些个飞机啊军舰啊之类的。所以报考这个专业,舅舅的影响是一方面,自己对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兴趣,就这样,我上了交大。
但是,大学过得很快啊!大学4年,现在要让我回忆这4年里面做了哪些事?很难。近几年我跟几个校友聊天,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,就说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都很难回忆起来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事,好像印象都很淡。什么原因呢,太单调了,就两件事:学习、吃饭,就三个点:寝室、教室、食堂。后来,我们毕业十多年、二十年以后再回学校,碰到的老师跟我们说,这20年来就77、78那两届是最用功的。当然,到第四年课程少的时候,做毕业设计的时候,我们可能也打打牌、下下棋啥的。但是前面三年半,是全部扑在学习上面的。大学4年很快就毕业了,还真想不起来做哪些事了。回头想想,我们当年都到什么程度了:毕业20周年我们同班同学聚会的时候,男同学女同学坐在一块说话,当时大家就说今天晚上说的话比我们那4年说的话还多啊!可见当年男女同学之间交流少得可怜。
我印象中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上完一节课,只要有听不懂的,一堆的学生围着老师问问题,老师下了课都走不了。这可能跟我们觉得进到大学很不容易有关。当时学校里同学岁数相差非常大,有我们这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也有岁数比我们大很多的成了家的,甚至有父亲上大学、小孩上小学的。一个班级的同学踏进学校以前什么背景的都有,除了应届毕业生以外,从工厂来的有当工人的、有当过车间主任的,从农村来的有插队下乡的。但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,就是求学的欲望都非常强烈。谁也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。不像现在的学生,抱负非常大啊。你要问当年我们大家有什么抱负,谁也没什么抱负,就有类似于我这种感觉的——从80几个人里面挑出一个人上大学——真不容易,一定要把学上好。我上中学时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,其中两个快班,我是一个快班的学生。你想想,十几个班挑出两个班的人,所以,在中学就感觉要争气啊。然后,又考上海交大,当时上海交大在全国还是很响的,就觉得一定要用功啊。就这样一步步走来,感觉自己很不容易,因此特别珍惜。说起同学们读书的刻苦劲儿,都疯了,夜里个别同学都学到凌晨一两点。班级里你这样做,我也要这样做,全班四五十人都学习到很晚,好像就应该这么做的。这跟社会发展有关系,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那么学的,我们出来以后,它确实没用上,我们也不会觉得遗憾,当时人们的思想就是这样。但是现在要重新再上一次大学,我肯定不会那样。因为社会已经不需要那样,不需要业务上面要精到什么程度,可能需要其它方面知识更广一点,需要在学校得到其它的一些锻炼。我们当时其他方面的锻炼,可能太少了。
听编教材的老师讲课
我们在交大的课程挺多的,一个学期大概十几门,一年下来二三十门,四年下来的话很多了,压力很大。单位里和我同来的别校毕业生,我说这些课程你怎么不学呢,他说学校没让我们学就没学。总体上,我感觉交大的学习氛围比较好,基础课程抓得很牢。我们参加工作当然会用到一些高深的东西,但是也离不开基础的知识,本科期间学的内容很重要。我们单位招人规定必须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,即使这样,有时候我做评委,我就是看他们本科的学习内容、学习成绩,研究生期间的东西看得少。参加工作,尤其是到了企业,如果不是做高深科研,本科阶段学的东西更重要,研究生阶段的反倒其次。
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相当不错的。学校有规定,编教材的老师第一年必须自己上台讲课。由于是刚恢复高考,那些编过教材的老师都在讲课,正好全部被我们赶上了。我们一看,这本教材就是他编的,听他讲挺好的。因为“文革”停了十多年课,十多年没出教材,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刚出新教材,我们之前的77届他们没赶上。等于老师们十多年以后重新编制的教材我们第一个拿到手里!老师花了很大心血,都讲到点子上了。读本科时的专业课本我全保留着,铅印本的,全套的!爱不释手啊,工作中时不时要用到的。我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年了,有时候还要把大学时代用的书本翻一翻。我现在跟年轻人讲业务,遇到想不起来的地方,我还翻一下我的课本,哦,书里是这么说的。
记忆犹新的大排面和假期旅行
我们读书是公费,自己就是掏点买书的钱,别的没有什么花费。我们那时候能吃啊,上海学生定量是34斤粮食,比市民高,但还是不够吃,家里月月还得寄全国粮票。那时候物价也便宜,我们刚入校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15块钱就够了,后来贵一些,20块也够。像我第一年入校的时候还有助学金,不是现在的奖学金,叫助学金,人人都有份,只不过多少而已。我从城市来的,家里有收入,家庭平均指标就高一点,指标一高呢助学金就少了,当然也给你一点,给9块钱。同学中有多的给28块5毛,那这就很好了,他们一学期家里不用寄钱就能生活了。那时候我拿了助学金,家里再每个月寄二三十块,加上学校的9块钱,有30多块钱,吃得很好。赶上节日或寒暑假,我还自己跑杭州去玩一玩,跑苏州去玩一玩,感觉很好。
我对学校里的大排面印象特别深。那个大排面,最早是一毛八,到毕业的时候涨价了,但是涨价之后也做得特别好。哎呀,大排真大,一碗面两毛五,我们的夜宵天天吃。最近几年我有时回学校,我同学杨建民说,走,出去吃。我说今天就咱们俩,咱们别跑外面去,咱们俩还穷讲究干嘛,就来一碗大排面,我们俩就去了。当时学校门口十字路口那里有个店卖汤包的,小笼包一屉五毛。我每礼拜天到那里买两屉,改善一下生活,再加一碗小馄饨,当时就好这一口。
我们那时候跑过的地方很多,几乎把上海市所有的公园都转了,上海周边很多城市都玩了。我现在碰到的这些年轻人,包括我儿子,寒暑假怎么老在计算机里折腾那个游戏呢,怎么外面都不想转呢,寒暑假就回家了。我们当时放假回家,买车票回天津的话,路途有3天时间,我可以中途下车,路过济南、路过南京,我就下车玩,玩完以后再上车回家。当然上车以后没座位了,但是那票不作废。你再上车,在有效期内抵达就行。我们都指着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玩。苏州啊,无锡啊,全转悠了。同学们都是这样的。也不用花很多钱。有说这次玩苏州花销大了一点,多大,10块钱,玩3天!掏出十块钱,一个地方能玩好几天呢。
那时从穿的、用的上面,看不出谁富谁贫。富一点,体现在吃的上面。我吃两屉小笼包,然后买了大排面,别人可能一周吃两次,也有的一周可能吃三次四次。就是这样一个区别,从穿着上面看不出来。从活动上也看不出来,你去周边转,全班同学都去过,都转了。总体上大家状况还是比较单一的。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的个别研究生开车的都有了。我们班里那时拿到28元助学金的同学,会感到很自豪。这个,你没拿到吧!你家里有钱嘛。我拿到了,因为我家就父亲工作,母亲没工作,还有3个弟妹,我穷嘛,我能拿到28元的助学金,等等。当时就比这个呀。现在比这个吗,现在一说家里没钱,那挺……说不出口的吧。
天南地北造就南腔北调
我们毕业属于统一分配,上学期间国家没收费,但是毕业以后必须听从统一分配。我是1982年毕业的,那一届上海学生的比例比较大,他们基本留在上海,上海造船厂、研究所比较多。我们北方的、还有一些偏远外地的,基本上都去了广州。去广州的大概有19个人,黄埔船厂5个,广州船厂14个。当时广州造船厂要了很多大学生,我们系就去了10几个人,加上其他系的,整个交大去30多人,再加上其他学校去的,那一年广州造船厂进了80多个大学生,这是建厂以来都没进过这么多人。我在广州船厂干了三年,第一年实习,然后分配到船舶研究所做设计,干了两年多。后来陆陆续续走的人很多。我本来就觉得离家太远,一看别人走,心里也萌生了走的念头,就调回来了。在广州的那三年,大家过得很潇洒,吃啊、喝啊、在周边旅游啊。虽然仅三年时间,但比在学校过得要红火得多,滋润得多。虽然钱也不是很多,50多块钱一个月,但是感觉很自在。这三年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。现在我回过头来想想,这三年其实对我后来帮助挺大的。虽然我现在做海洋工程设计,但是我对船舶比较具体的认识其实是在那时候形成的,这段工作经历以后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。
1985年10月,我调到石油部门工作,回到了天津。中海油在塘沽有个做海上石油设施设计的工程设计公司,我调回来就在那个单位工作。从那时到现在,基本上有30年,我一直从事海上石油设施设计的工作。海上石油设施里面分两大类,一类是固定平台,那不是我们做的;我做的主要都是浮式系统,漂浮的东西,比如说,钻井船、FPSO、系泊系统等,我在石油系统做的大部分就这一块的东西。在塘沽,我干了13年。
1998年,我来到中海油研究总院,一直干到现在,还是设计工作。在石油部门所做的事,面要比造船厂的面来得大、来得广。我当时在造船厂只是做一个产品的设计,什么万吨船、散货船、游船,都是单一产品的设计。到石油部门所做的事,面就广了。海上生产装置,还只是油田生产里面的一个环节。这一块的工作,对开拓视野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在石油部门这么二十多年干下来,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?甭管是在广州那边干还是后来到石油部门这边来干,船舶或海洋工程这个专业,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重新再上大学、再选专业,我还选这个专业,海洋工程。如果就这个专业选学校,还选交大。目前全国做船舶和海洋工程这块的学校很多,从北边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始,一直到南边的中山大学、武汉水运啊,还有天津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等,总体上感觉交大出来的学生还是比较被认可的。
我说话有个很大的特点,很多人听不出来我是什么地方的人。南方的人听我像北方的人说话,北方的人听我像南方的人说话。要是我不做自我介绍,很多人不知我是什么地方的人,口音比较杂。我住过的地方都是属于方言很有特点的地方,像我小时候在福州住过,福州话现在简单的能说一点,听是没问题能听懂。读中学在天津,呆了五年,天津话在北方语系里也是很有特点的。然后大学跑上海去了,上海那一块的话也很有特点。毕业以后,去广州造船厂在广州住了3年,然后又到天津塘沽住了十几年,然后再跑到北京来住了十几年。就说全国各地方言有比较明显特点的地方我都呆了一下子,造成我现在说话的口音,真是南腔北调。
大师=积累+灵感+机遇
我们班有两个设计大师,我,还有胡可一,他是2008年评上的。我与他四年中有两、三年还是同寝室的。我被评上船舶设计大师的时候,我跟同事说,我评上大师还并不是最感到兴奋的,我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呢?第一届船舶设计大师评选时,我也参评了,在场的有我同班同学4个人,两个参评的,还有两个评委。胡可一是这一年评上的,我是2010年评上的。老实说,我当时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并不是最优秀的,但后来在这个领域里有一点成绩。有时候很怪,不光在我们这个行业,我也听到别人说学校学习成绩好的,很难说在今后工作业绩上是表现最出色。现在我们说这个大师也好,各个厂里的总工、总师也好,我们倒退30年,搁到学校里头,我们这几个人都不显眼的。
学术上、工作上,能取得一些成绩,表面上看,哎呀付出好大心血,其实也很简单,这30年做一件事儿,反复地做,你就是专家。你到任何地方去说去,谁也说不过你,谁也说不到你那个深度,这时候你的权威性就显现出来了,在业内就是不一样了。我长期都是干这行的,人家干了10年就转行了,半途就转了,或者是干了10年甚至干20年,后面才有新人跟着一起干,他干的时间没那么长,经验没你那么丰富,遇到的问题没你那么多,到任何一个场面去,比如说汇报、谈总体方案的时候,他说不到你那么深和广。那你就是专家啊。所以说,有时候也不要把专家看得太神秘。所谓大师,就是一直干这件事而已。打比方我要去干飞机设计,我要干30年我也是专家。就怕你干半截儿的,你改了。这跟老中医一样,要有经验的积累。必须慢慢地积累,积累到一定程度上,你的水平自然就高了。当然有时候,还需要有一些灵感。你会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,这就是非常让人佩服的时候。这跟每个人有点关系。当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办法,走投无路的时候,你要是能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它解决掉,周围的人就不得不佩服你。作为一个从技术层面走出来的人,你还得有这种解决问题的灵感。另外的话呢,还得有机遇。经常的说七分努力三分机遇。有时候,机遇来了,正好赶上了,这样的话,可能设计大师帽子就戴到你头上了,就这么个理儿。但是,前面的20年、30年,你肯定是要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。当然,能够在一个领域长久地坚持下来取得成就,多多少少跟个人的兴趣有点关系。就是说,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上面要是长期属于被动的,出不来好东西。要取得成就,多少得有一点主动性、有一些兴趣。
在海洋工程中遨游
学校的学习以及在广州的一些见识,给我后来做的工作打下一些基础。到了塘沽以后,我就开始接触海洋工程了。接触海洋工程对我来说,有点陌生也并不陌生。为什么陌生呢,因为我们属于浅海开发,浅海开发固定平台用得更多一点,浮式系统用得少一点。
造船工程,到我们毕业那一年,在我国已经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。从李鸿章开始,国人对船舶行业多少有些了解了。但是我国海洋石油开发历史非常短,在国内做海洋工程的不多,大多还是从做船舶工程转过去的。不过,我到塘沽时人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。那几年我是有什么活干什么活。今天钻井船有问题了,我就帮做个设计、做个改造。明天还要计算稳性什么的。我在船舶部门印象比较深的是,在广州大部分计算还是靠计算器算,到了塘沽这个部门用软件的机会更多一点儿。当时我下了好大的精力学软件,叫奥斯卡软件,是从美国进口的,要搞海洋工程必须要掌握它。我当时花了好大力气去掌握它,学到后来,去美国培训回来的几个人,用这软件的熟练程度还没有我这个没培训过的人用得好。我下功夫下到那个份上,最后别人都不怎么能用得来,我却把它用的很好。人家一看有什么事儿,你给算一下,活越做越多,软件也越用越熟。从设计上来看也是如此,你接触的事儿越多,攒的经验也越多。平时工作就这些起重船、三用工作船、钻井船……跟油田开发生产有关的这些装备,做一些计算啊、分析啊、方案论证啊,油田开发我也都做了一些。那段时间的工作,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都属于打杂的活儿,但是你想做更高的设计,这一步你是必须走的。
我到塘沽以后接触到了曾恒一,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,应该来说我进了海总,学到了这些知识,还有做了这些浮式系统,他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我在塘沽前后做了13年,其实做的项目油田很多,十来个。比较有特色的几个项目给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。比如说当年开发某个油田的时候,要做一个单点设计,这单点设计是国外一个专利产品,国内是不会设计也不会生产的。当时我们与美国一家公司搞联合设计,跟他们做了两个月,但是有些东西人家是保密的,不提供给你,很关键的一条特性曲线,它是保密的,原理不告诉我们。我在那里接触了一点,回国以后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,把那东西给推导出来了,结果与他们一样。现在想想,有些人家封锁的技术、专利,看着很深奥,其实有时候并不难,是我们自己深入不到里面去。其实外国人能想到的我们一样想得到。我们能想到的外国人一样能想得到,就这么一个道理,只不过看你花的功夫大小而已。如果一看到这个就不敢介入,想退却,那这不行,这时候必须硬干下去。你不要指望去问别人,那个年代在那个状态下,没有人能比你知道的更深,只有你自己咬了牙往前走。要想取得比较专的一些技术,你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。这个单点设计上,计算原理突破以后,一算,外国人是这样的结果,我也这样的结果。完成啦,就这么简单!过了十多年,我们年轻人也接触这块的东西,我把当年的东西拿出来。他们说,这问题本来是用高级软件计算的,你怎么把它用解析法给解出来了,用解析法、作图法给做出来了。我说外国人是这么想,我也这么想,就做成了。我说原理都在我这几张纸面上画着了,他们看了都特服气。我对他们说你们有时间的话,得做一些手工的工作,不要太相信那个软件,现在引进的这个那个的大型软件,里面有些核心的东西是个黑匣子,你根本整不明白。
后来到了这边总院以后,慢慢地我做的事儿就更专一点儿。经常做的就是FPSO,就是浮式生产储油装置,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做这一块事儿。到总院以后,做的面更广一点,油田开发上FPSO这一块浮式系统做得更多一点。刚来的时候做的那几个FPSO都挺有特色的。比如说渤中25-1的浅水效应——那是我做的一个863课题,我同班同学、交大船院院长杨建民也一起做。那时候他下的功夫也大,我下的功夫也大,下了很大功夫,还是出点成绩。因为渤海水比较浅,用大型浮式储油装置,很多人都担心会触底,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,告诉他们,不会触底,我们甚至把极限值给求出来了。全世界都在由中等水深往深水发展的时候,很多人都忽略了浅水,其实浅水问题也很大。而且浅水问题只有中国人去解决,别人不会跟你解决。什么原因呢?在别人的海域里没有浅水的问题,一说都是100米水深以上,只有中国渤海有十多米、二十米水深。我们要在这里开油田,自己不解决谁帮你解决?只有我们自己去解决!所以大家都往深水做的时候,我们做了浅水。这是我后来到了北京以后做的一件事,比较花时间、花功夫。
在渤海,我们还做了旅大油田的一个开发项目。那个项目按常规来说,应该是搞固定平台结构人做的事,但最后是让我做浮体专业的人把这个事给解决了。什么事呢?就是说固定平台里面,常规的储油罐都是圆形的,我们现在做的罐体是方形的。这个理念是借用了别人的一个设计,但只是看了一下,所有的参数都不知道,我们回来后自己去琢磨、查资料。我就把船舶里面储油舱的概念给挪到这儿来了,相当于跨了一个专业领域,把别的领域的东西借过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因为油轮船舱都是方的,船舶储油舱也都是方的,四四方方的、长方体的,没有圆形的。石油行业做的罐都是圆形的,圆罐的受力比较好,但是摆在平台上面不行,因为平台本身是四方的,平台的边边角角就浪费了,要做成方形利用率就高了。但是这里面实际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,全世界都没有这个规范、也没有这样标准、更没有参考的材料,我们只是看了人家一个东西,然后自己回来琢磨:把船舶里面的这个规范移过来行不行?把另外一个行业规范移过来行不行?前后折腾了好长时间,最后做成了这个事!
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组块浮托安装工程。海上平台分两步骤建设,一是导管架,二是组块。导管架建好后,它上部组块是分布实施,工艺设备啊、生活楼啊、电站啊,都做成一个设施组块,很重的,几千吨、上万吨。过去都是用起重船把它吊到平台上,一块块吊起来再焊接,因为起重船的起吊能力不大,需要切成小块。现在做法是整个给焊在一块儿,一万多吨,用驳船一次性从海上托过去,往导管架那儿放,我们叫浮托安装法。南海的一个气田开发要采用浮托安装,没那么大船,要去国外租用大船,人家说可以,但光租船不干,你得把这个工程交给他干。这叫捆绑式,明显的是宰你。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做、自己论证。有一天,我们专业的一个年轻人找我,摊手,这个事怎么办,怎么弄也解决不了!听完他汇报,我说我现在也没办法,我下去抽根烟再说。到楼下抽了两根烟以后我上来跟他说,这事这么办:常规的驳船是长方的,我们在首部船宽切窄,尾部加宽,整个问题解决了。他说您什么时候想出来,我说就抽烟的功夫想出来的。有时候啊,就一件事突发奇想的时候,它就是3秒钟的功夫!就想出来一个好的解决办法。当然,论证这3秒钟的点子,可能需要3个月。最后做下来,从上到下都说这个方案好,就按这个方案做。就这解决了大问题!要不非得到国外去租船,花大价钱不说,工期还不能保证。
说实在的,任何人做了几十年,他都能说出一大堆东西来。现在我跟别人比,无非就是我头上扣了这么一顶帽子。其实,只要我们干这行当干了30年,你让其他同学去说,也一样,也会有这样、那样的经历。你们有机会采访他们,他们也一样能说出很多经历。
有钻牛角尖的劲头
我们大学一年级,高等数学、普通数学、线性代数,什么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学都上的,理化各种实验都做的。我当时还问老师:都上大学了,怎么还做酸碱盐实验啊?这我们在中学都做过,所以想不明白,但是课程确实就这么安排的。实际上,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后体会这些基础知识还是蛮有用的。特别是物理、数学,基础扎实的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太大了。我一直是物理好,高考的时候物理就差点考满分了,我有这样一个特点,很复杂一个东西,我看一眼,就能把它简化成一个普通的物理方案,这样的话再转化成数学公式就容易多了。
我们刚毕业以后出现出国热。人家来单位一门心思学外语,工作相对干得少了。我们单位每年还都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学习好的到国外去留学,1980年代中后期想搞开放,送一批人出去,他们回来以后可以开拓事业,想法很好。当时确实这么做了,现在来看回来的是极少数。但是当时好多人是把精力放在出国上,我的精力放在工作这儿:一是刚才前面说的国外进口的软件,别人培训过,我没培训过,结果我攻克了;然后赶上海洋工程里的单点设计,有机会跟国外专家一起做设计的时候,想把这块东西弄会,也做了一些事。当时周边的气氛不是做这个,但我去做了这个,结果一看,哦,挺好。
我做事呢,还真有点钻牛角尖的那个劲头,如果今天问题想不出来,可能睡觉都睡不好。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有这种感觉,就是当这个人钻进问题的时候,这个事做不出来,连吃饭都在想这件事,走路都在想这件事,甚至做梦都在梦这件事。这就说明钻进去了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遇到问题时容易放手,我这东西可不会啊,你得告诉我。我前两天跟年轻人做一个课题,交给他们作业,他们摊手,实在没办法做,这太难了。我说难到什么程度,你有没有吃饭还在想这件事儿,做梦还在想这件事儿。他说还没有,我说那还没到位。你必须给我下功夫、给我干,你跟别人干可能没有这个体会,你跟我干必须干到这个份上才行。因为我做过一些事,有过这个经历,知道它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干海洋工程这行当的人很多,但是要钻到这个类似于牛角尖的程度,就没有太多人了。
善用集体的智慧
我是这样的,要是学术上遇上一些事,我有钻牛角尖的劲头。但是,在讨论大层面上东西的时候,我会尽可能让很多人比较容易地接受我的观点,我能把我的想法说得非常透。做成一件事,这一点很重要。我经常说,这件事我不是有十分把握,只能说它有七分的把握,我说要是大家能帮我把剩下那三分的把握给我说出来,咱们这个事儿就能做得成。要是说没有人能帮我,我也会把那七分的把握说出来。还有一点,所有人都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,我的话比较容易平衡各方观点。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能力和锻炼。因为,很多时候不是最优的方案被选中,而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方案被选中。当自己认为最优的方案可能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二到三,98%的人接受不了,那么,这个方案就没用。这么说吧,任何人做事都不是完美的,表面上自己看到这方案非常优,那不行,肯定还有不少难以被自己发现的缺陷。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优的。
做学术我喜欢内向,是这样的,做小事、不是很大的工程的时候,单打独斗就能实现,人一多思维反而乱了。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工作,我还是偏向于多说一点儿,发挥大家的才能,一起把项目做出来。因为我们这个石油领域的项目跟别的领域的项目不太一样,毕竟在海上,投资大,牵涉的部门很多,涉及的专业多达几十个,面很广,又跟国家的政策、法律关系很大,这些原因造成石油部门项目的特点,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。不像设计一个杯子、眼镜盒,一个人就能做了。把一个油田开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,很难说某个人在里面的贡献有多大,它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,这种项目是整个工业基础的集成。
对交大学生的一点建议
对现在的年轻人,我是这么看的,不能埋怨他们浮躁。你想想,一个人刚出校门,家里也没有多大资金资助,他们面对成家,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子在哪里。不用说他们,要换我的话呢,我也会想这个问题。所以说,现在的年轻人走向社会,肯定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,尽可能在愿意干的行当里面找一个收入高的单位,这是很自然的。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,让他们去了解、去适应这个社会。
当然现在有一件事儿,我也看不过去。最近几年,交大来我们这里的人不多,什么原因呢?大概是2006年、还是2007年的时候,毕业生挑得太厉害了。面试时他说确实要来,我们决定要他了,他又不来。我们申请个指标不容易,比如申请100人,当这边有5、6个人不来了,这时重新再去找就不可能了。好了,这几个指标全部浪费了。前后连续两年招的交大的学生大概有6、7个出现这个问题。一趟、两趟,后来我们的领导决定,交大的学生不要了!我跟杨建民说,你跟毕业学生说一下,这种事儿少做,你可以挑可以选,但是尽量想好了,你肯定有来的意愿再来面试,真是一点也不想来,你干脆也别报名。当你这样做完以后,给后面的师弟师妹造成一个很坏的影响,我们单位曾经连续三年交大的学生一个都不要了。
我是这么想的,没有当面跟他们分析,其实他们后来挑的那些单位,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都知道,只是一个短期效益。当时来看那个单位或者收入比较高,但是长期来看肯定还是我们这里好。当然,不管年轻人他们怎么想,但确实给后面的师弟师妹们造成了影响。
为母校留下一点东西
对一个比较知名的学校来说,应该有一些东西留下来。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,就说当年邓小平到欧洲去留学,在一所学校勤工俭学,过了五六十年再去那个老学校,再去查他的学习成绩单,还在。人家那学校说,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保留下来,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物,这就是档案工作做得很好的例子。作为一所老牌大学,这方面是需要认真做一下。
你们这次访谈的意义很大,大在哪里呢?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特点,后来的人不知道从前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过来的,会很想了解这些东西。像我对曾恒一院士一样,他是我们的上级领导,我们也经常接触,其实我也很想知道,曾总1958年进学校,1961年毕业,他当时是怎么学习的?他当时有什么故事?有什么特点?年代相隔不久的,情况会差不多。比如说1982年毕业的学生同1985年毕业的学生,差不多。但是间隔上十多年、二十年呢,跨度大了以后就不同了。后面的学生可能就想,这些老学长他们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?他们的人生路怎么走的?校友访谈工作的意义就在于这里。
至于我们被采访者本人怎么样,我感觉这都是次要的。当你找某个人的时候,他只是体现这个人的一些特性,但是,这些人串在一起的时候,就形成了一条有价值的珠环。我在工程项目里,也这么说,你每做一件事,或者在某个地方有创新、有突破的时候,你其实只是一颗珍珠。只有珍珠多了,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,它才形成项链。值钱的在于项链,而不是单个珍珠,就这么一个道理。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特色,对学校来讲,被采访的人多了,就能把这些特点和特色进行总结,能从侧面体现出学校的一些特色。对以后的学生也好,对做校史研究也好,能留存一些东西。有兴趣的人翻一翻,哦,曾经某一些人,在某一个年代,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,我想是这样的。我们愿意配合学校回忆一下当年的事,为学校留下一点东西,至于我们个人在工作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,我想这是次要的。
(摘自《思源·起航》,马德秀主编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)